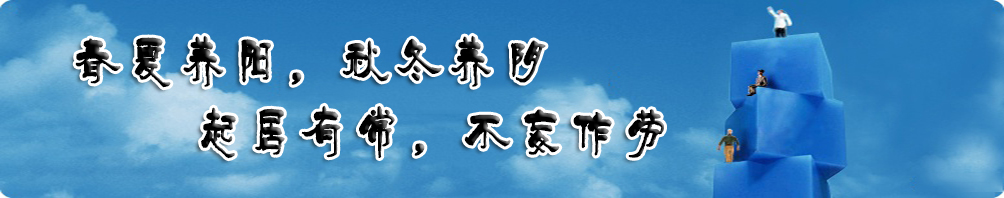
古籍研究管子的养生思想
《管子》一书,相传为管仲所著,实为战国时期齐稷下学者托管仲之名所作,其中亦有汉代附依部分,现存七十六篇,共分八类。其内容庞杂,融汇了道、名、儒、法诸家思想以及天文、历数、與地、经济、农业等知识。书中亦对养生益寿之道进行了精辟透彻的论述,这部分内容尽见于《心术》、《内业》、《白心》等篇章之中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养生文化遗产,时至今日,《管子》的养生学说,亦多有可资借鉴之处。
首先,《管子》非常重视心神在养生中的重要作用。认为“心之所依,君之位也;九窍之所职,官之分也。心处其道,九窍循理”(《心术上》)。明确指出心在人的脏腑关窍中是起主导作用的,心的功能正常,九窍自然各司其职,其功能亦正常。因为“我心治,官乃治。我心安,官乃安”,故“治之者心也,安之者心也”(《内业》)。又因心主神明,心由神养,神旺则心气亦旺,心气旺则脏腑关窍之气皆旺,功能协调有序,身心则健康无病,所以“神者至贵也”(《心术上》)。
由此,《管子》得出了意欲养生,贵旺心神的结论。而旺盛心神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欲、无为、静神,因为“凡心之形,过知失生。……心神内聚,以为泉源。泉之不竭,表里遂通;泉水不涸,四肢坚固”(《心术下》)。“知”,此指心欲,欲多则损命,心神内聚则如泉水有源,取之不绝,人体表里通畅,四肢健壮。所以《管子》主张“虚其欲,……扫除不洁,……是故君子不怵乎好,不迫乎恶,恬愉无为,去智与欲。……其处也若无知,其应物也若偶之”(同上)。此乃“静神之道”。所以,善养生者,当以静为道,“静乃自得”,“心能执静,道将自定。……节欲之道,万物不害。……能正能静,然后能定”(《内业》),明确提出了“静则生慧”的观点。
由于影响安心静神的主要因素是七情的困扰,所以《管子》继而又提出了平和喜怒,调畅情志,以养心神的主张。指出:“凡人之有生,必以平正。所以失之,必以喜怒忧患。……凡心之形,自充自盈,自生自成。其所以失之,必以忧、乐、喜、怒、欲、利,能去忧、乐、喜、怒、欲、利,心乃反济。彼心之情,利安以宁,勿烦勿乱,和乃自成”(《内业》)。
所以,善养生者,当“节其五欲,去其二凶,不喜不怒,平正擅胸”(同上)。而去除七情困扰的具体方法则是“止怒莫若诗,去忧莫若乐,节乐莫若礼,守礼莫若敬,守敬莫若静。内静外敬,能反其性,性将大定”(同上)。对此《管子》还提出了“凡人之生,必以其欢”的乐以忘忧,畅怀蠲郁的养生观点,“大心而敞,宽气而广……宽舒而仁,独乐其身”(同上),以此去烦解忧,自可益寿。
其次,《管子》认为“精存自生”,主张保精养气,以延性命。由于神是由心血所化生,心血又源于精气,所以《管子》认为“精也者,气之精也。……精存自生,其外安荣,内藏以为泉源,浩然和平,以为气渊。渊之不涸,四体乃固;泉之不竭,九窍遂通”(《内业》),意即精存则有命,外荣而内盛,气旺浩然,体窍皆健,自可延年益寿。所以要人们当惜精如命,保精养生。《管子》还认为天地之精气,合而为人,“和乃生,不和不生。……充摄之间,此谓和成,精之所舍,而知之所生”(同上),所以保精之法,不仅要保养体内之精,还要和合天地之精,也就是今天气功界所说的采天地之精气以养生益寿。
第三,《管子》还对于调节饮食进行了阐述,指出:“凡食之道,大充,伤形而不藏;大摄,骨枯而血冱。充摄之间,此谓和成,精之所舍,而知之所生。……饱则疾动,疾则广思,……气不通于四末”(《内业》),过疾过饱都会影响气血的通畅,于健康不利。所以《管子》提出了“食莫若无饱”,亦勿过饥,少食为佳的主张,这样则可调和脾胃,通畅气血,健身益寿。
第四,《管子》认为,凡诸养生之法必宗之于“道”,务须循“道”才为跟本。而“道也者,动不见其形,施不见其德,万物皆以得,然莫知其极。故曰:可以安而不可以说也”(《心术上》)。“夫道者”,在人“所以充形也”(《内业》),人之形体及生理均遵循着“道”的规律,而“道”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,“所失以死,所得以生也”(同上),“凡道,必周必密,必宽必舒,必坚必固。守善易舍,逐淫泽薄,即知其极,反于道德”(同上),只要做到“善心安爱,心静气理,道乃可止”(同上),遂即可得养生之“道”,进而收到“修心正形”之效果。即只有掌握事物规律,事事做到执中,不偏不倚的得“道”之人,才能做的到。
综上所述,《管子》的养生思想是重视心神对于生命的重要作用,提出了“恬愉无为”、去欲弃情、“精存自生”的养生法则,主张通过静神正心,无为制窍,“节其五欲,去其二凶”,常保乐观,调和饮食等,以达养生之目的。(马孟昌)
(图片来自网络)